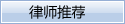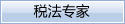孙笑侠:生活逻辑与法律思维的差异
法治首先要求法律人具有专业的法律思维。然而这种法律思维常常不能被普通人理解,有时法官的话还容易惹起众怒。这里存在多种原因,比如有的法官会违法裁判,又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并且是终极裁判者,所以现在许多社会矛盾都集中到法官身上,这是大家可以观察得到的原因。法官的话易惹众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容易被察觉的,这是一个职业技术的因素,即法律人独特的职业思维因素。近年来发生的很多法律热点案件或事件引起争议,除了个别法官违法裁判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法律人士和非法律人士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所以大众在监督司法的同时,还需要了解法官正常的职业思维,最好能给予理解和尊重。
民众一般是从一个结果、从结论、从实体上来判断的。法律人的思维则是从程序、证据、规则的角度来思考的。因为法律对法律人是有要求的,所以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能像大众那样考虑问题,他们的思维和大众的思维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支撑他的职业主义的理论。简言之,民众的思考是根据生活逻辑;而法律人的思考则是根据技术理性。
那么,职业主义的思考到底有何特点呢?
首先,法治要求法律人用一些法律术语来思考问题,我们称之为法言法语。所谓“三句不离本行”,你同一个法官或者律师交流的时候,会发现搞法律的人就是三句不离本行,说出来的都是权利、义务、责任、违法、自首,通常是用专业的术语进行推理、思考。法律人把现实生活形形色色的事物转化为法言法语,就和法律上对应的规则接轨了,就可以进行解释、推理和判断了。
其二,法律人考虑法律问题时,坚持一种“向过去看”的思维习惯,尊重过去的事实、规则。人们在普通问题上的思维都具有前瞻意识,向未来看,比如一个普通股民会觉得今天跌不要紧,或许明天会有转机,这就是常规的生活习惯——向未来看。可是法治要求法律人在办案时必须向过去看。比如说,学法律的人,拿到一个案件总是会说,这个案件是3个月以前发生的,那3个月以前的情景是怎样的,他会用证据来重构那个情景,他会用业已颁行的法律(而不是未来新规则)作为依据来处理,预想的未来规则不是有效的规则。法治就是按既定规则办事。
其三,法律人坚持“程序优先”的思考。法律人考虑问题的时候,通常不会先入为主地说结论,而会说程序怎么样?日常生活中也有会用到程序,比如一个家庭3个人正考虑国庆节到哪儿去玩。爸爸说东北挺好的,挺凉快;妈妈说去东北太辛苦了,还是在家呆着算了;年轻人说去新马泰玩。3个人观点不一致,这就产生了“纠纷”。观点不一致怎么办?父母和儿子可能都论证了一大堆理由,尽管很充分,但都是从实体上讲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毕竟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嘛。我们为何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用程序解决呢?“石头剪刀布”就是程序的方法。它一下子就把结论给决出来了。有一句话叫“愿赌服输”,程序排除了其他的思考。最后妈妈赢了,尽管爸爸和儿子的观点可能很正确,或有合理的成分,但是程序已经决出了,你们再有道理也无效,这就是程序。
其四,法律人在“情”和“法”两个要素之间进行抉择,会有一套法律方法来解决它。法治会要求法律人作出清楚的选择——在法律范围内对“情”做权衡。“情”字很复杂,情为何物?中国人讲的“情”主要有四种:第一是情理,第二是情感,第三是情节,第四是情面。法律上承认的是情理和情节,所以古话说“法本原情”,一般不承认情感和情面,所以有“法不容情”的成语。而非法律人会把案件中纠缠着的各种“情”混淆起来,在法律判断上就复杂了。
其五,法治要求法律人追求的“真”(真相、真实、真理)和客观世界的“真”不同,它是程序中的相对的“真”。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真”,但是法律人追求的“真”有一点不同,是追求程序中的“真”,和事实上的绝对“真”不一样。探究案件真相是侦查员的事,法官不是侦探,更不是科学家,一般不用侦探或科学家的方法,不用科学家的理念去探索真相,而是用双方列举的证据来重构一个程序意义上的“真”。所以法律人的这个“真”和科学家以及大众讲的“真”是不一样的。法律上的“真”是程序中用有限的证据来构成的“真”。比如,缺乏有罪证据就是疑案,要遵从“疑案从无”原则。
最后,法治要求法律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清清楚楚地作出一个结论,不能模棱两可。在日本法官那里,他们称这个思考是“一刀切”的思考,即要求说出“黑”或是“白”,“曲”或是“直”,“是”或是“非”,这是法治要求法律人必须给出的最后的说法。